中国商报报道(记者于贵华)“老师流着泪讲,学生流着泪听。”中国解剖学会副理事长、大连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主任隋鸿锦如此形容解剖学课堂。
这并不是说解剖学老师和学生的情感比常人更丰富,而是教学环境让人容易落泪。“人体标本需要福尔马林固定,福尔马林的刺激性很强,所以我们上课真是鼻涕眼泪一起往下流。”隋鸿锦说,这种环境,导致很多人不愿意从事解剖学。
1992年,隋鸿锦第一次接触到生物塑化技术。他意识到,这项技术对解剖学的教学很有价值——它可以改善解剖学的工作环境。此后,他的人生与事业,便与这一技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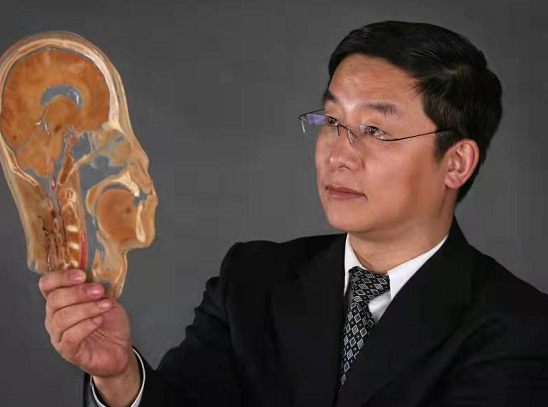
最大胆的科普公众人物
“不同于传统手段,生物塑化技术不采用甲醛作为防腐剂,而是用一种高分子材料,替代标本中易腐败的物质,比如水、脂肪等等,达到长期保存的目的。” 隋鸿锦解释道,生物塑化标本是干性的,没有刺激性气味,易于保存,保存期还很长。
1994年,隋鸿锦专程到德国去学习这项技术,把这项技术带回国内。最初,隋鸿锦团队利用生物塑化技术,给各大高校做人体标本。后来随着标本数量越来越多,他认为,生物塑化技术不仅可以很好地改善解剖学的教学环境,还能让人体标本能走出学校,走入公众的视野,比如——人体展览。
1543年,人体解剖学的鼻祖维萨里发表了著作《人体构造》,第一次从科学角度阐释人体结构。他邀请了著名艺术家为著作绘画插图,其中包括很多惟妙惟肖、具有生活场景的解剖标本。维萨里希望通过这些插图,减少人们对人体标本的恐惧感,使这些标本能够走近大众。
“在设计标本时,我专门设计了一个名为农夫的标本,造型模仿卡尔卡的插图。我觉得,这一方面体现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是在向维萨里致敬。”隋鸿锦说。
2004年4月8日,隋鸿锦在北京举办了国内第一次塑化标本展览。质疑声随之而来,甚至还有谩骂。
“这让我非常吃惊,因为在我看来,人体标本的展览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1936年同济大学庆祝29周年时,就已经有了人体标本的展览。20世纪80年代,很多医学院校也把瓶装标本拿来展出,舆论评价也很不错。” 隋鸿锦陷入沉思:为什么我们在21世纪办的这个展览受到了很多批评?“后来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一项全新的技术。一个全新的事物,推向社会之后,社会了解它、认识它、到最后接受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令他欣慰的是,也有不少观众留言对展览表示支持。一些专业性媒体,也发表评论呼吁给人体标本更多宽容。
2004年底,隋鸿锦被《科学时报》评为当年“科普十大公众人物”之一,获评“最大胆的科普公众人物”。
“其实,我没感觉自己大胆,我只是尽了一个解剖老师应尽的责任。” 隋鸿锦说。

每一个展品,都要讲故事
“展览,绝对不是简单地把展品放在那就行了。每一个展品,都要讲故事。”这是隋鸿锦关于展览的经验之谈,“展览一定要跟人的情感、文化联系上,激发观众最深层、最温柔的情感。”
在他看来,人们都想了解自己的身体、关心自己的身体。但在生物塑化技术出现之前,大部分人没有机会看到人体标本,只能通过书籍、图像、视频来了解,很难得到直观的感受。如今,人体标本的展览为公众提供了直观了解自身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展出的内容和大众的主观印象不同。提到人体展览,许多人想到的词是恐怖、血腥……但当观众真正看到这些标本时,会发现它是有美感的、有动感的,还有教育性。而且,我们一直强调,展览不能冷冰冰的,要能打动观众内心当中最温柔的部分。
隋鸿锦团队在人体展览中加上了病理标本,通过对比,让观众了解到疾病多么可怕,健康多么脆弱。例如一组展品,一个是没有吸烟人的肺,一个是吸烟人的肺。颜色的对比让观众震惊,很多人看过之后当场表示再不吸烟了。
隋鸿锦团队还在展品旁边摆上一个弃烟箱,让大家把烟扔掉。同时搞了一个活动——让来参观的孩子和自己的父母签合同,保证以后不吸烟。
“通过这种方式,人体标本不再是冷冰冰的展品,而和观众的生活、情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隋鸿锦看来,这样的展览陈设,绝不止步于单纯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内容的发掘。“内容的发掘非常有难度,不是花钱就可以,它需要用心和创新,而创新也是科学家精神很重要的一面,只有创新才能发掘出有生命力的内容,形成自己的特色。”
在几次演讲中,隋鸿锦都提到了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一个人体展馆的故事。“那个展馆只有300多平方米,但内容很丰富,他们发掘出很多遗体捐赠者的故事。”
其中一个叫徐益勤的捐赠者,就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48年,徐益勤38岁,了解到医学院缺少遗体,表态要捐赠遗体。徐益勤很长寿,去世的时候106岁。这距离他决定捐献遗体,跨度近70年,最终在2016年实现了捐赠。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人体科学馆的馆长,把这些故事发掘出来,把徐益勤的女儿请来,给观众讲她父亲的故事……
“通过这些具体的事例,观众了解到每一件人体标本,不是简单的物品,而是曾经和我们一样有呼吸、有心跳、有情感的人——这对每一个观众是一种心灵的冲击。”隋鸿锦说。
动物标本,同样也要讲故事。隋鸿锦团队做的《巨鲸传奇》展览,便是如此。
2016年2月14日,一条鲸在江苏如东搁浅了。经过4年多的时间,隋鸿锦团队把它做成了标本。这个展品长度接近15米,重达40吨,创造了两个世界纪录——第一,它是世界上第一只被塑化保存的抹香鲸;第二,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塑化标本。
为了这个展览,隋鸿锦团队准备了很多鲸的故事。比如,第一个展厅就讲鲸不是鱼。他们在这个展厅当中摆了两个庞然大物,一个是鲸鲨,一个是小须鲸,通过这两者的对比,让观众感受到鲸鱼跟鱼的区别。

构筑“书—馆—网”立体化科普模式
在从事生物塑化技术研究和解剖学教学工作多年后,隋鸿锦努力探索并精心构筑“书—馆—网”立体化科普模式。
在图书方面,隋鸿锦不仅编著了高校教材教辅之外,还投入大量精力编辑出版多部科普书籍。《人体的奥秘》便是其中之一。以《人体的奥秘》为基础,出版发行场馆展览图册共4册、10多种文字、21个版本,总发行量超过100万册。
在博物馆领域,隋鸿锦于2009年创立了生命奥秘博物馆,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普教育基地”“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还获评中国科普联盟“科普研学十佳品牌”。每年,他都会走进博物馆进行几十次义务讲解。“每当看到孩子们好学的眼神,我就非常开心,因为他们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激发了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就是为国家播种下科学的种子。”
在网络科普方面,隋鸿锦设立了近70个“科学星球”微信群,每周义务上生物微课堂,传播爱护自然,保护动物的理念。他还每年赴多地开展十余场科普讲座,进行现场讲解。
2019年1月,隋鸿锦编写的科普丛书《生命奥秘丛书》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中国科普界的最高奖。
“斗转星移,不知不觉,我已经做了近20年科普工作,成为学生们眼里的‘老教授’。作为中国解剖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深知自己担负着向全社会科普人体知识的重任。同时,我也意识到,科普工作必须依靠广大科学工作者携手努力,共同推进,要着力培养专业的科普队伍,教会未来的科学家如何做科普。”做好科研之余,隋鸿锦带着课题组的年轻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开展科普工作,并利用学会平台召集全国医学院校的师生参与到解剖学科普事业中来,践行解剖学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的使命。
“中国科普事业依然任重道远。作为一名科普老兵,我将一如既往、努力不止,把做好科普工作当作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记在心中、扛在肩上。” 隋鸿锦说。

